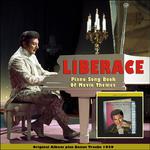本字幕由TME AI技术生成
在这以前
曾国藩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应付科举考试上
目光被限制在硬制石文
也就是八股文和试帖诗的狭小范围里
做官以后
他虽然曾摸索过做古文和诗词的方法
但终属支离破碎
对学术问题和治学方法缺乏系统的了解和基本的常识
因而对唐建的话感到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大有顿开茅塞
一心耳目之慨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在给贺长林的信中也说
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生主想自从静海先生游
稍乃初使止归
他在写给朱棣的信中回忆自己治学过程时
讲的更为详尽
凶少时天分不甚低
绝后日与庸闭者处
全无所闻
翘辈茅塞久矣
尽得一二两有知有所谓精学者
精济者
有所谓功行实践者
使之泛韩可学而至也
马骞
韩愈亦可学而至也
程朱亦可学而至也
慨然思劲敌前日之屋
以为耕生之人
以为父母之孝子
以为诸棣之先导
可见唐建等人对他的鼓舞之大
影响之深
曾国藩按照理学家的严格要求进行修身养性
是从道光二十二年冬开始的
本来在上一年夏天
唐建向他传授读书之法的时候
同时也谈到了减身之要
要他熟读诸子全集
即以为课程
并举倭人的例子
说
近食河南倭艮丰前辈用功最堵
每日自招至寝
一言一动
坐坐饮食
皆有札忌
或心有私欲不克
外有不及俭皆忌出
希望他引以为榜样
将读书和修身结合起来
同时进行
但曾国藩并没有完全照办
尽管他每天专心阅读诸子全集
却并未做修身札记
却未做静坐功夫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
曾国藩向倭人请教修身之道
倭人告诉他
严几功夫最要紧
倭人说
言子之有不善
未尝不知是言己功夫也
周子曰
积善恶
中庸曰
钱虽辅以一孔之召
刘念台先生曰
普动念以知己
皆为此也
失此不察
则心放而难收矣
还说
心之善恶之己与国家治乱之己相通
最后
倭仁告诉他
必须写日课
并且要当即写
不宜在因循
倭仁所说的己
就是思想或事物发展过程中刚刚露出的苗头
所谓延己
就是抓住这些苗头加以认真的研究
从而发现其发展趋势和利害关系
其克己之法
就是通过静坐
札记等自省功夫和相互讨论
将一切不合封建圣道的杂念消灭在危露苗头之时
以使自己的思想沿着封建圣贤所要求的方向发展
并且将学术
心术
智术连通一气
使学问得到增长
道德水平得到提高
从而逐步体验和学习治理国家的本领
这就是理学家一套完整的修齐治平的理论
回去以后
曾国藩就按倭人的要求写修身日记
他每天静坐半个时辰
写下自己各种不合封建圣道的思想和行为
并经常将自己的日记拿给吴庭洞
冯卓怀
陈远衍等人阅读
交流心得体会
曾国藩还常把自己的日记送请倭人批阅
倭人的媒批无非是一些批评鼓励之语
开始
曾国藩对静作思很不适应
每静坐未久则昏然睡去
即离梦境已半天过去
对此
他总是又气又恼而无可奈何
只好在日记里把自己痛骂一顿
第二天再重新开始
直到十多天之后
才慢慢的习惯了起来
然而他这样搞了两个多月
就变了主意
原来曾国藩本就体质孱弱
由于每天搞得太紧张
不久就得了失眠症
整日的无精打采
勉强又坚持了二十多天
突发吐血之症
从此身体虚弱
心情不畅
再也不想刻苦修行
做一个专治理学的学问家了
他在病后不久
写信给弟弟们说
吾如体气本弱
耳鸣不止
稍稍用心
便觉劳顿
每字思念
天既陷我以不能苦思
是天不欲成我之学问也
故近日以来
一颇疏散
即今日若可得一差
能还一切旧债
则将归田养亲
不复恋恋于吏禄矣
是不是曾国藩改变了对理学的看法
从此以后不再搞理学了呢
不是
他在同一封信中对他的弟弟们说
读经以严询义理为本
考据名物为末
自西汉以至于今
识字之儒
约有三图
曰一理之学
曰考据之学
曰词章之学
各执一图
互相诋毁
兄之思义
以为一理之学最大
义理明
则公行有要
而经济有本
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
还说
此三徒者
皆从事经史
各有门径
吾以为
欲读经史
但当研究义理
则心医而不分
是故经则专守医经
史则专属一代
读经史则专注义理
此皆守约之道
确乎不可议者
可见曾国藩并没有轻视理学
弃之不问之意
他对理学在儒学中的核心和指导地位并无怀疑
其读书方法也仍然坚持唐建的说法
他的转变
主要是在治学内容上
改变了理学与古文的主次地位
自道光二十年以来
曾国藩就追随桐城派学习古文诗词
并初步摸到一点做文章的文道
养成了对古文的浓厚兴趣
所以虽然唐建告诉他
诗文此曲皆可
不必用功
而他仍不能忘情
他在给刘荣的信中情不自禁的写道
国藩即从庶君子后
语文莫论而浅避之姿
兼视华躁
号司马迁
班固
杜甫含于王安石之文章
日夜以诵之不厌也
可见他这时的做法是主攻理学
监制古文
虽整日忙于读书写字
静坐写心得
仍没有放弃对古文的研究
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和实践
曾国藩发现理学家的这一套治学和修身办法不适合自己的情况
遂改贤更张
将研究理学的目标仅限于领会其精神实质
即所谓粗使己字
不敢为非以导大力
他不再盲目的仿效别人
搞什么静坐自省
修身日记一类的
其治学的内容也改为主攻古文
兼治理学
一年后
他在家书中对弟弟们说
于近来读书无所得
唯古文个体诗自觉有进境
将来此事当有所成就
数月以后
又更为自信的说
若如此做法
不做外观
将来道德文章必粗有成就
可见他这时候的主要精力
集中在了钻研古文诗词上
并略有进展
颇为得意
但是他并没有放松对理学的学习和个人修养的要求
不过只是改变了办法而已
同时
他治理学也不再限于阅读程朱的著作
开始追溯而上
阅读张载
周敦颐的书
并对他们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只是在道光二十二年末及其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对考据学仍抱轻视的态度
把它当成了细枝末节
明确表示
考据之学
无无取焉
曾国藩学习文字训孤
是道光二十六年的事情
这年九月
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
携去段誉才所著说文解字一部
随手翻阅
当时汉阳刘传营也住在这里
刘传营至古文经学
精通考据
曾国藩便向他请教
刘传盈也正为考据学无荡于身心的修养而感到苦恼
遂向曾国藩学习理学
于是二人经常相互学习
取长补短
就成了好朋友
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营的交往
受益匪浅
不仅使他由此懂得了考据学
弥补了学识上的欠缺
而且使他进一步开拓了眼界
提高了认识
在学术上走上了全面发展的道路
他在给刘荣的信中
表达自己在学术上的见解和志向时说
于汉
宋两家构颂之端
皆不能左坦以复一哄与诸如重道贬文之说
犹不敢雷同而苟随
而欲兼取二者之长
见道既深且薄
唯闻复真于吾磊
同时
在治学上
曾国藩也不再独宗程朱
而是由程朱上述到了周敦颐和张载
尊奉孔
孟 周
章为儒学正统
将程朱理学和许正汉学一概归之于不无偏颇的支流旁系
他说
能深且薄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义者
孟氏而下为周子之通书
章子之正蒙许政
亦且深薄而殉孤之文
获失则岁诚诛
亦且深博而止士之语
获施则爱
自己治学则上者扬起于通书正盟
其次则笃士司马迁含愈之书为二子诚义
深博为颇窥古人属文之法
以上这两方面
都明确的表现出曾国藩在学术上独树一帜
自成一家的思想
这是曾国藩治学思想上的一个大飞跃
对当时学识的增长和以后在学术上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在京求学期间
曾国藩在学术问题上
除向唐建涡仁
刘传营等请教外
还经常与吴廷洞
邵遗臣
何贵珍等人进行讨论
他们在京师都有些名气
这些交往活动
不仅使曾国藩增长了各方面的见识
也大大的提高了个人声望
名称重于京师
这也是他得以迅速发迹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