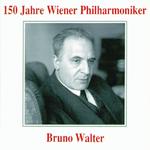本字幕由TME AI技术生成
我从小在一个航天部下属的军工单位家属院儿长大
回想起我童年呢
我总是能想到院子里那一片广阔的杂草丛生的大操场
我的童年有一多半是在那里玩耍度过的
可好景不长
我们厂子因为不与时俱进和出现了几个贪得无厌的厂长以后
厂子逐渐变得一天比一天不景气
厂子的几个领导看到自己的灰色收入越来越少
便打起了这片我最喜爱的大操场的主意
他们要利用这一片土地盖楼
上报之后
上边竟然鬼使神差的批了批文
并拨下了一笔巨额的工程款
这笔工程款大部分被几个领导中饱私囊之后
就开始了他们的豆腐渣工程
建筑队简直犹如天降神兵
前一天我们几个小伙伴还在大操场玩儿
一夜之后
大操场已经被工程队围了一个严严实实
并开始打地基
我们小的时候
电脑还没普及
计算机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工人家庭简直是不可触及
而丢沙包
捉迷藏这种毫无冒险精神的游戏
我们是瞧不起的
大操场虽然被围了起来
但围不住我们几个坏小子的心
犹如五色旗般红白蓝相间的塑料布围城被我们啊撕了一个粉碎
那时候大操场刚开工
地下挖出的地基就像一条条的战壕
而挖出来的土没被及时运走
堆在旁边形成了一个个的小山坡
当时的施工队管理体制很松散
我们几个坏小子成天在施工现场玩也没人能管
还偶尔轰过我们几次
不过该来我们还来
日子久了
施工队的人也就没人搭理我们
对于地上的地基我们就用来玩地道战
旁边的土坡我们就用来玩上甘岭
整天呢
玩的叫不亦乐乎
回家的时候个个啊
都是灰头土脸的
在我们小的时候就听大人们说过
我们住的这一片地方
之前呢
就是一片乱葬岗
葬也就是不管有棺材的没棺材的
是不是人的
死了都埋在了这儿
随着施工的深入
各式各样的棺材开始逐渐的浮出土面
民工们显然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把埋在土里的各种颜色棺材挖了出来
我们几个小朋友岁数都很小
正是好奇心泛滥的年龄
一看到有新鲜的东西
赶紧围了上去
这些民工也真够猛的
开着铲车把一大片棺材都给铲碎挥走
那时候的景象到现在还存在我的脑海里边
只要我翻开记忆一想
眼前就立刻浮现出那一片景象
棺材碎了一地
碎木头和死人身体各个部位的白骨散落了
整个大操场是一片狼藉
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情是
这些死人的陪葬物也掉落了满地
有铜钱
烟斗
瓷瓶瓷碗的
当然啊
这些都是碎了的
还有一大堆的白色纸钱
我们几个坏小子一股脑的跑过去哄抢这些地上的陪葬物
我记得当时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拿了不少铜钱啊
烟斗啊什么的
欢欣鼓舞的贴着地上的死人头骨是满载而归
到现在回想一下
小时候啊
那胆子真够大的啊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我小心翼翼的把这些从地上捡的宝贝揣进兜里
回家之后看到我爸
我自豪的从兜里边掏出一堆铜钱给我爸看
我爸就问我这些铜钱是哪儿来的
我说啊
是从大操场挖出的棺材里边捡的啊
我清晰的记得我爸的第一反应就是抡起胳膊重重的甩了我一记大耳铁子
扔了
打完我之后
我爸凶狠的喊了一句
转身就走了
我捂着脸呆在了原地
我们这群小伙伴们的父母性格几乎一样
都姓棍棒底下出孝子
我的家庭也一样
挨打是家常便饭
不过没用
越打越皮
可在当时
这记耳光打的我可是莫名其妙
直到长大懂事儿之后
才慢慢懂得那一次我爸为什么打我
捡死人的东西是会招来厄运的
我也不敢违背我爸的命令
小的时候啊
爸爸对我来说就是天
只要我犯一点小错误
爸爸都会对我拳打脚踢
打的我是七横八素
我当时就赶紧打开窗子
把捡来的陪葬物给扔了出去
后来大操场的地基越打越深
也越来越威胁
工程队加严了管理
坚决不允许建筑队以外的杂人进入
我们这帮小孩也难逃法眼
那段日子真是无聊透顶
从此啊
我们就迷上了火
确切的来说
是点火玩儿
几个小朋友凑在一块儿
从全院搜刮来白色的塑料泡沫
点燃塑料泡沫以后高举
被融化的塑料伴随着火焰一滴滴的滴在地上
滑落在空中的时候
我们能清晰的听到哗哗的火焰的声音
不知道为什么
小时候一听这种声音就能让我们热血沸腾
后来点塑料泡沫觉得没劲儿了
就开始点纸
点木头
点一切能点燃的东西
我记得很清楚
大操场被丰厚的第一个年头到年干
马上临近春节
我们小时候的春节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枯燥乏味
所以耐不住寂寞的我和几个小伙伴在某天晚上终于又偷跑进了大操场
钻进去之后
找到一片拔脚的空地
三个人蹲坐在一团
开始点燃废报纸烧了起来
一张一张的
火势也逐渐变大
我们看着火光
暖着手
聊着天儿
那天没有风
浓烟飘散开来
在工地的大灯照耀下尤其明显
工地上的大灯是蓝色的啊
幽蓝幽蓝
烟雾缭绕
当时我脸是朝外蹲着的
只有我能看到他们两个人身后的那一片空地
我们烧着烧着
慢慢的
我一抬头
看到远方幽蓝的灯光和烟雾当中
有一个人的轮廓冲我们过来了
那个动作很缓慢
当时我也没在意
我以为是捡破烂儿的
然后低头继续烧着报纸玩
还在跟其他两个人啊
嘻嘻哈哈
那时候也小
也不知道害怕
哎
这要放到现在
看到那东西第一眼我都已经跑了
我当时就继续烧着报纸
烧了一阵
我又一抬头
这一下我是真的慌了
因为远处那个人的轮廓逐渐的清晰了起来
哎
半点儿不爬瞎
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
我现在脑子里浮现出当时那真实的情景
只见那个人披头散发
衣服是白色的
很宽大
脸看不清楚
因为还有一段距离
更让我当时觉得很奇怪的是
那个人
他不是用走的
而是飘的
真真实实就是飘着的
而且离我们是越来越近
我忍不住的叫背对着后面的两人
让他们赶紧回头看
那两人回头的时候
那个东西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他
就暂时称他为那个东西
就在我不注意的一刹那
他已经 啊
离我们非常非常的近了
仍然看不清脸
但是绝对是一身白衣
披头散发
没脚
那两人回头一看
立刻都炸毛了的妈呀一声怪叫
紧接着我们三个人是撒丫子就跑
一路谁都没说话
疯跑着各回各家
第二天白天
我们又碰面
说起昨晚的事情
那些所见所闻
仍然心有余悸
那晚我如果啊
只是我一个人看到
我可以不信啊
我可以找借口说自己当时眼花了
可当时我们三个人同时都看到了
而且那么近的距离
总不能三个人同时眼花吧
现在我们都长大了
仍然是联系平凡的好朋友
每当我们工作之余聚在一起的时候
一提起这件事儿啊
仍然会谈的是津津有味
从那一天起
我就变成了有神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