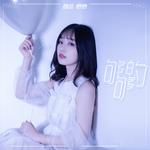本字幕由TME AI技术生成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雪山大地作者
杨志军
获奖
四季风声第九章团圆
这里有流不尽的水
长河无限
这里有说不完的话
扎西德勒一句话的长河
汹涌了多少年
滚动的是爱波
明亮的是情衣一
父亲说服索难分掉牛羊和草场后
过了两个月
州委通知泉州生产队以上的干部汇聚信托公社参加现场会
王石书记在会上把沁多公社大大表扬了一通
说他给阿尼玛青州的牧业改革带了头
引了路
督促所有生产队三个月之内必须完成草场的划分和牛羊的分配
诞曾书记虽然反对
但也只能装在心里
表面上还是点着头
算是强迫自己维护了王石书记的威望
王石说
现在一大二公的集体解散了
牛羊是自己的
草场是自己的
生活也是自己的
谁能把日子过好
谁就是英雄好汉
谁家的牲畜多
牛奶多
酥油多
账房大
皮袍新
谁家能定期足量完成上交的菜畜定额
谁就是模范
木染此后的分处分场就像一阵风
一场狂飙突击的运动
仅仅过了二十天
阿尼玛荆州就在泉州范围内基本实现了联产承包责任制
王室派人把父亲和索南叫到州上
在一个刚刚开张的回族人饭馆里请他们吃饭
碰杯的时候说
感谢二位
真是帮了大忙
泉州六个县
四个县反对大包干
两个县虽然不反对
但不知道怎么搞
问我具体的办法
老实说
我也不知道
只能拿你们做样板
你们的分配是合理的
办法是成功的
闹事的
提意见的
没有牧人除了高兴还是高兴
索南说
我哪里知道什么叫打包干
都是强巴阿爸的主意
我就是照他说的
给牧人一户一户的讲道理
遇到难缠的
非要跟别人抢夺一等草场的
我就把绝八爷爷搬出来
我说
我是爵巴德基的孙子
你们不知道吗
不服气
你们就去找他伸援
看他到底向着你们还是向着我
王石说
看来是强八的办法
爵巴的权威所难的嘴
索南说
欧呀欧呀
书记说的对
王石又问父亲
你就打算这样下去
真的不当干部
不要工资啦
我有这么多牛羊
还顶不上工资吗
顶氏肯定能顶上
但前提是风调雨顺
万一遇上旱灾雪灾呢
既然要做牧人
那就得不怕灾难
大不了一贫如洗
从头开始的事
我还做的少嘛
那就随你
我算是仁至义尽了
说着从提包里拿出两个半导体收音机
这是奖励
是我私人送给你们的
索南不敢要
父亲说 拿上
索南说
那我得送书记一头牛的
要脸
王石说
已经送了
但父亲毕竟不是一个传统的牧人
或者说
他是整个阿尼玛荆州最具先锋意识的牧人
至少
他不是人们司空见惯的那种牧人
两年后
父亲的牲畜翻了一番
变成了一百多只羊
二十多头牛
其中五头是带牛犊能挤奶的毛姆牛
有一天
他骑着日嘎
带着洛洛送给他的一只两岁多的铁包金藏獒
在自己承包的一万亩草场上走了一圈
粗略一算
便抓住两只肥羊
牵到帐房跟前
用绳子绑住嘴
憋死了他们
然后扒皮掏葬
用羊皮包了起来
第二天
他留下藏獒多吉守护牲畜
自己带着羊肉飞马去了沁多县
他来到炖猪小卖部
跟站柜台的炖猪聊起来
炖猪说
你看现在货架上的货物是不是比过去品种多了
因为进货渠道多了
除了省商业公司
还有西宁糖酒副食品公司和阿尼玛星州贸易公司
哪一家便宜都是公家单位给的价
差不多是糖酒有时会便宜一分两分
那还得看人是老客户才行
小卖部要是能直接从生产厂家进货
肯定便宜多了
那我绝对不敢降八案不就是直接跟厂家打交道的结果吗
我天天听收音机
现在好像没有投机倒把这一说了
人家把帽子藏起来
等着你伸头嘞
千万不要上当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
又说
我是个牧人
再过三年
我的羊就会增加到六七百只
还不算牛
可我的草场是不会增加的
只能越来越紧吧
那怎么办
屠宰
然后卖掉
这是唯一的办法
我宰了两只羊
想在你这儿试试
卖不掉等于我送你
卖掉的话
我们四六分
蹲猪摇头
你又想害我了
分给我四成
万一怪罪下来
我就有四成的罪
那咱们一九开
你只有一成的罪
不干
一成的罪也担不起
父亲再三说服
顿珠再三拒绝
气的父亲转身就走
又返回去
借一把斧头总可以吧
他拉着日嘎
拎着斧头去草地上把两个羊科郎卸成碎块
插上自己的藏刀
抱到县政府门口
在羊皮上摊开
吆喝起来
羊肉 羊肉
谁要羊肉便宜
加上新鲜
一个小时后
羊肉告清
但对父亲来说
重要的还不是这么快就卖完了
而是这几年县委县政府进了不少外来的干部
买羊肉的基本都是这些人
他收起羊皮
正要走
就听有人在身后问
羊皮卖不卖
扭头一看
是个年轻人
你要不是我要
是有人来小卖部打听有没有羊皮
原来此人是县小卖部的主任
强巴案发生后
小卖部的主任换了好几任
换来换去都不认识父亲了
父亲问
是你先给我钱
还是你把羊皮卖了再给我钱
我不知道给你多少钱一张
八块
两张都要的话
十五块
你可以十块钱一张卖出去
行啊
我也这么想
羊肉要不要
价钱不能高
而且还得新鲜
那当然
我们是牧区
到处是羊
价高了谁吃你的
就是今天我出手的这个价
一斤七毛六毛吧
我八毛卖出去
赚两毛的差价
父亲接过羊皮钱
扮出一副吃亏受损的南过样子
说 好吧好吧
三天后
父亲再次来到县城
直奔县小卖部
看到柜台上已经没有了羊皮
就知道卖出去了
年轻的主任竟没说
我还得给你两块钱
为什么
我说十二块一张
寻思人家会讲个价
没想到那个人放下钱
拿起皮子就走
小卖部我承包了
赚多赚少都是个人的
赚太多的话
雪山大地会不高兴的
说着把两块钱放在了柜台上
父亲收了钱
说
那你就叫晋美小卖部嘛
晋美是无有无故的意思
他觉得那是吉祥的
晋美说
我正在给县政府说
要是同意
我就改掉
说着跟父亲出去
从马背上卸下了两个羊科勒和另外两张羊皮
过了几天
父亲又来小卖部时
羊肉和羊皮都没了
弟美问
这次你带来多少
一个羊克郎
一张皮太少了
多送点
他要来羊肉牛肉都可以
父亲问
没有人干涉吧
我们又不欺行霸市
谁会干涉
父亲就像跟人争辩一样说
对呀
我一个牧人
卖自己的羊肉又怎么了
只要价钱公道
卖给你
卖给他又有什么区别
难道非要我卖给公家
再用公家卖给老百姓才行得通
进美瞪着他问
谁说你什么了
没有
我自己说我自己呢
一个月以后
炖猪小卖部也开始出售父亲的羊肉
牛肉和羊皮牛皮
父亲了解到
要是两个小卖部一起卖他的肉
一天就能卖掉四个羊柯了
两天就能卖掉一个牛壳了
说明整个县城的牛羊肉需求量大着呢
可是他已经不想宰杀自己的牛羊了
主人的飞马奔跑让日嘎有些莫名其妙
怎么可以把风撞得唰啦啦响
很久以来没有这样的声音了
没有了和空气急速摩擦式的疯狂
没有了草原在堤下迅速消失的欢快
日子平庸的有些憋闷
连大喘息大嘶鸣大出汗的机会都不见了
但是今天
久违了的鞭子又开始凌空旋转
主人的大腿一次次夹紧
它的亢奋和爆发就像从主人心里腾起的风
推动着阳光的暖流
让所有的金色朝着一个方向前进
他感到主人的情绪里微妙的混杂着忧愁
焦急和希望
于是他也拿出了一匹马的忧愁
焦急和希望
让脸肌尽量绷紧
让眼睛里的忧郁透过一层潮湿的薄膜变成了荧光朦胧
让四体的摆动节奏分胧
急速而不狂妄
他看到漫漫草潮像两条并行不悖的河
涌动着激浪
带着夏天的清爽和温度
从不断掉下地平线的太阳里溢出
咆哮而来
浩浩而去
漂浮在上面的是盛放了一层的奇形怪状的花
父亲说
日嘎拉
你说这样行不行
到底什么行不行
他并不说出来
好像日嘎天生就能揣度主人的心
他一想他就知道了
父亲不时的抬起头来
望着草巢扑上天空时的浩茫
望出了绿色地毯被黑牛群和白羊群折断时的遗憾
望出了草原由于各家承包而被草皮墙和铁丝网隔断的簇霞
天上的云朵还是地上的杨朵
都是白色
一片又一片
这边的云朵
那边的杨朵
木草的蔓延依然无边无际
但中间总有黑色和白色的凸起
有牛羊
也有土石
草原烂了
终于见到了绝霸的帐房
他滚鞍下马
丢开缰绳
让日嘎去吃草
示意跑过来的每朵黑不要声张
然后仰躺在草地上
冲着天空喊道
绝吧啦
绝吧啦
凭感觉
他知道绝巴走出了帐房
又说
你现在变得没出息了
整天守着你的牛羊和米玛
牛羊生了不少他们的儿女
却不见米玛也生下你的儿女
学霸说
米玛
你快来听这个天上掉下来的人在胡说八道什么
你给他说
你的肚子里是什么
米玛来了
微挺着肚子
笑着把一碗酥油茶放在父亲的头边
父亲扭头闻了闻热腾腾的香气
说
酥油放的太少了
难道你家的毛母牛还没有喂大
牛犊就已经不下奶了吗
爵霸家的牲畜多数在桑杰那里
他和米玛只放养了一小群羊
两头毛母牛和三头牛犊
父亲指的是他家的牛犊太多了
超过了养育能力
学巴说
天上的雨水有多少
我家的毛母牛的奶水就有多少
你操的心比牛毛还多
没有一个跟你相干
父亲坐起来
端碗喝了一口酥油茶
说
我没说错吧
你现在没出息了
人这辈子操心的事有多少是跟自己相干的
学巴瞪起眼睛说
草动是为了招风
花开是为了留种
我知道你是个难得消停的人
又有什么事想到我了
赶快说
现在不说
到了桑结和索南跟前一起说
父亲一口气喝干酥油茶
想单手撑地站起来
结果又坐下来
伸手让爵霸把他拉起来
又说
走吧
马大那里有两瓶青稞白酒
我们去桑杰那里喝个够
爵霸摇摇头
说
你强吧
带给我们藏族人的都是好东西
就是这个白酒不怎么样
你不是也喝过吗
喝了我才知道
肚子还没胀就开始晕三倒四了
那也不是我带来的
州上的我不知道
信多县第一次有白酒
就是你从省上进到小卖部的
父亲想想也对
喊道
维多黑
好好守着米玛肚子里的小绝吧
大绝吧
要跟我喝酒去啦
梅朵黑照例轰轰轰的回答着
虽然都在自家的草场
但夏天的游牧走得远
父亲和爵巴骑马走到黄昏
才看到桑杰一家的大帐房
当周吼叫着扑过来
父亲下马抓住他的两只前爪
看看帐房一边的牛羊
说 当周啦
桑杰的牛羊真多
你以后就不要管了
让狼吃掉一些才好
当周汪的一声咬住了他的胳膊
却不真咬
蹬着皮袍袖子摇头晃脑
桑杰走出帐房
快步迎过来
对爵霸弯了弯腰
说
阿巴拉好
扎西德勒
西天的云彩落到你脸上了吗
气色这么好看尼玛
阿妈好吗
他肚子里的娃娃好吗
我已经到阿尼琼贡献了一羊肚子酥油
观雀家阿妮说
雪山大地祭坛前的灯会一连点上七天头胎
爵霸家的这个娃娃吉祥的就像草原本身
长长的没有头
宽宽的没有边
又转向父亲说
我看到日嘎喘的是白气
使了太大的劲才会喘白气
连日嘎这样的马都拖不动你了
你发福了
父亲说
我虽然胖了点
但也没有胖成一座山
倒是你
胖的眼睛睁不开
看不清人和马了
日嘎根本就没有喘气嘛
你是心里高兴才这么说啊
欧耶
日子一舒坦
话就多了
快快快
帐房里坐
回头一看
爵霸丢下大黑马已经进去了
刚刚放牧归来的索南把几头毛母牛拴到挡绳上
跑过来从地上捡起大黑马的缰绳
又从父亲手里接过了日嘎的缰绳
父亲说
由他去吧
不要拴他
左南说
我担心他会去别人家的草场上找母马
那还不好
又不是人
有什么好
要是人家的草场上繁殖起日嘎的后代
到处都是好马
超过了我们怎么办
父亲上下打量着他
奇怪的问
你开始放自家的牛羊了吗
怎么有这样的想法
公社变成乡了
主任变成乡长了
听起来好听
就是越来越没事干了
为什么
牛羊和草场都是各家各户自己管自己
集体没有了
政府也用不上了
我过问多了
人家还会嫌弃我
不如回家放自己的牛羊
父亲点点头
说
光放牛羊可不行
你可以腾出手来干别的
别的
还有什么
我今天来就是说这个的
坐下来说吧
父亲回身从日嘎背上卸下马
大连抱着进了帐房
索南去掉日嘎和大黑马的脚子
放开大黑马
在党绳上拴住了日嘎
日嘎拒绝这样的待遇
他从来都是自由而放浪的
同时也严守着一匹乘马天生的纪律
主人一旦需要
喊一声或吹一声铁哨
就会丢开自由
包括爱恋母马的自由
奔跑而来
他又是甩头又是拉扯
没等索南走远
就已经脱缰而去
索南追了过去
日嘎撒腿就跑
边跑边冲他扑扑扑的
放屁
索南说
你这个没良心的
强把阿爸把你惯坏了
等你让我家的母马全都怀上了橘子
我就给强巴阿爸说
把你善掉
现在你给我听着
到了别人家的草场
吃草可以
流种是不行的
父亲把两瓶白酒拿出来
先用牙齿咬开一瓶
斟满卓玛拿过来的四个碗
端到爵巴
桑杰
索南面前
又对卓玛说
姐姐啦
先上点风干肉下酒啊
爵巴说
别给他上风干肉
等一会儿吃新鲜的
把曲拉端上来
一把曲拉
一堆手抓两碗赞粑
五碗酥油茶
他说的是曲拉能开胃
那就曲拉
不吃风干肉也好
父亲说着
端起碗
用右手无名指蘸一点
朝上一毯
再蘸一点
朝身边一毯
再蘸一点
朝下一坛
爵霸说
这就对了
人手上无名指用的最少
也是最干净的
给雪山大地敬酒最吉祥
可是有的人现在开始用又长又脏的中指蘸酒了
不懂规矩
父亲说
其实都一样
最要紧的是心诚
说着双手捧碗
我们四个人难得在一起吃饭喝酒
是第一次吧
爵巴说
亲人疏
疏人亲
狼和狼不吃
狗和狗不食
张杰说
要是尼玛在就好了
家里的男人就全了
爵巴说
就算尼玛在家
男人也不全
还有才让
江阳 洛洛
还有西宁城里的老爷
父亲说
欧爷
我们这是一个大大的家
藏族汉族都有
什么时候能把人凑齐就好了
又问
尼玛去哪里了
左南说
到县上接扑斥去了
富赤是青海民族学院藏文系的大学生
放假后会去姥爷姥姥家待几天
再由姥爷或者央金把他送上回沁多的长途客车
怎么光说话不喝酒
父亲说着喝了一口酒
其他人也都喝了一口
桑杰脸上的肌肉朝一起搓去
难看的就像一堆有螺纹的牛粪
父亲说
不至于吧
这么难受
桑杰说不出话来
半张了嘴
呵呵的往外吐气
像是嗓子里正在着火
左南说
阿爸是第一次喝白酒
我也是第一次
爵巴说
我第一次喝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但这个酒还是要喝的
以后人和人打交道
不会喝酒
恐怕人家理都不理你
父亲说
我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就开始喝了
爵巴问
汉族人为什么把酒酿的这么猛
不会绵软些吗
就像我们藏族人的青稞酒
父亲说
汉族人喝白酒有几百年的历史
藏家老早喝着不过瘾
桑杰咳嗽起来
他好像对白酒格外排斥
索南小心翼翼又喝了一口
哈着气说
我就不信了
他能把我辣死
看我把他一口气喝到肚子里
打个滚变成水
一泡尿尿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