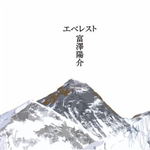本字幕由TME AI技术生成 第五十六集 老猫现在很虚弱 站不了太久 他招手让四宝把它搀回值班室 其余的人也都跟了进来 因为谁都不知道如何收拾这个残局 只好等老猫发话 老猫在值班室中一屁股坐下 掏出一根烟点上 皱起眉头想了想 问亮子 你敢外可急贼的搜吗 亮子答道 还行吧 干嘛呀 老猫说 你先去外科找纱布跟酒精给手雷爆炸脑袋 再弄几件衣服给他穿上 打发出去 亮子 老猫不再说话 呲牙咧嘴的低下头 不住的伸手抓挠双腿 李斌在一旁是站也不是 坐也不是 他明白此事不好收场 不知道老猫会如何罚了他 即使是在仅有半条命的老猫面前 他也不敢嚣张放肆 老猫半晌没吭声 像是在思考着什么 其实他这个病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和浑身瘙痒 挠到了见血 这才觉得好受一点 他虚弱至极 挠得累了 软塌塌的歪在椅子上 有心无力的说 小斌 你够黑 我不得不佩服你呀 心狠手辣的让人肝儿颤 可我也看不起你 你这叫人神共愤你知道吗 且不说他手雷是地雷的亲兄弟 你怎么连太平间的死人都不放过 你可真是玩出圈儿 我老猫是有今天没明天的人了 今今天脱鞋上炕 明天还穿上穿不上都不好说 到时候我不也得躺在总医院这个太平间吗 你是替我躺道来了是吗 李斌眨了眨眼 不置可否 老猫接着说 我这么一个新将就木的人 想给你跟墨斗分个对错也有心无力了 要说当初我挺看好你们俩的 以为你们将来会在城里独挡一面 上次我也听说了 你们跟洗头 老哑巴的冲突 有马涛在场 我就没必要再出头了 因为马涛 地雷他们跟我都是一抹子的 当时 你们确实给咱城里的玩闹长脸了 可我万万没想到 这才几年呢 你们俩就闹掰了 掰的还那么彻底 你们俩是傻叉吗 现在外边是个嘛情况 风声那么紧 别人都知道躲了 你们就非得在这个时候分个鱼死网破 别说我吓唬你们 动上手没轻没重的 万一闹出人命 你们不也得挨遭吗 能子真活腻了 想来下边找我去 不想 那我可纳了闷儿了 你跟我说句实话 李斌 你跟墨斗到底是应该嘛呀 打的你死我活的 老猫虽然强打精神 但是越说气力越短 到后来气儿都喘不匀了 四宝忙给他妈子后背顺气 李斌在一旁低头不语 腮帮子咬得一鼓一股的 可他真不敢和老猫顶嘴 他才出道多久 老猫 地雷 马涛那一波人曾经风云一时 老猫一搞把子 废了三傻子一条腿的情形 至今历历在目 老猫见李斌如同一个大蔫曲一样闷不吭声 挥手把桌子上的酒瓶子扒了下去 酒瓶子啪嚓一下摔得个粉粉碎 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 李斌连忙赔个不是 猫哥 这祸是我惹的 您看怎么办 我挺您的 老猫的脸色这才见缓 哎 自己拉出来的屎橛子自己擦 没别的 先把手雷放了 给人家送回去 再抓紧时间联系一下墨斗 你跟他上我这来一趟 只当你们小哥俩成全我 给我老猫一个面子 成不成 李斌惹不起老猫 万一老猫死前放出一句话去 他以后甭想在城里混了 迫于无奈 只好应允了老猫的要求 先把手雷送回家 早上五点多 东方泛出了鱼肚白 亮子已经把太平间收拾好了 小义子也开来了那辆二幺二吉普 其余几个人把手雷头上的伤口进行了包扎 并且让手雷穿上了临时找来的衣服 可他两个眼睛直勾勾的 对周围的人视而不见 犹如一具行尸走肉 任凭国栋和司令把他架上二幺二吉普 没有一点反应 老猫对李斌交代了一句话 小斌 以后做事儿别太绝 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记住了 面子是别人给的 脸可是你自己的 走吧 李斌没说话 上车一拍小义子肩膀 示意出发 小义子一踩油门 二幺二吉普开出了四平西道 驶向新兴路 小义子在吉普车上问李斌 咱往哪儿开 李斌仍在想老猫刚才那两句不阴不阳的话 越想越觉得别扭 听到小义子问他 当即吼了一句 哪儿远往哪看 小义子见李斌正在气头上 一句话不敢多问了 国栋和司令也不知道李斌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光看李斌的脸色 跟所有人都欠他八百块钱还还不上似的 谁也不愿意自讨没趣 因此再没有一个人开口发问 经过一天一宿的折腾 众人身心俱疲 不知不觉打上了瞌睡 李斌再次睁开眼时 小义子已经把二幺二吉普开到了荒郊野外 李斌一边透过车窗四下张望 一边问小义子 这怎么啊地儿 小义子说 敢过赵顾里 前面是虚撞的 李斌听说过照顾李 却没来过这边 一看周围长满了蒿草 一个人也没有 他让小义子找个地方停车 又大声的喊道 都你妈醒醒 司令 国栋连同手雷都被他这一嗓子惊醒了 车子在一条土道缓缓停下来 李斌把脖子缩到大衣里面 推开车门跳了下来 绕到车后边 拉开车门 用胳膊搂住手雷的脖子 皮笑肉不笑的说 我本想找个地方挖个坑把你活埋了 念在你上有老下有小 这回先放过你 但有一点你记住了 不是我李斌没有胆量办你 而是我动了恻隐之心 另外还有一点 如若你胆敢包官 我进去了不要紧 我外边的弟兄可饶不了你 滚吧 说完 他一脚把手雷踹下车 坐回副驾驶 对小义子说了声 走二幺二 吉普排气冒出一股子白烟 怪叫声中疾驰而去 很快消失在了荒野中 李斌的路数只有他自己清楚 刚从医院出来的时候 他想按老猫说的 把手雷扔到家门口 不过老猫最后损他那两句 是他心中窝火 别看李斌在老猫面前唯唯诺诺 其实他心里根本不服 脑子一转 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法子 我可以给你老猫一个面子 放了手雷 却不会完全按照你说的意思去做 那样的话 你老猫有面子了 我李斌的面子怎么办 我把手雷扔在荒郊野外 这么大冷的天儿 手雷单衣薄裤 身上带伤 能不能回去全看他自己的造化 冻饿而死可怨不得我 于是 他让小义子把车往郊区开 可见李斌的用心有多么的歹毒 手雷让李斌他们扔在荒郊野地 周围全是开挖 一眼望去看不到尽头 甚至找不到一条柏油路 八十年代的天津市区远没有现在那么大 咱打个比方 当时从城里往西走 出了西营门大街 走到现在的中环线 再往西走 那就是西营门大队的庄稼地了 更何况徐庄的赵顾里呢 手雷身上有一件较为厚实的劳保大衣 里边却是单衣单裤 在旷野上让大西北风一刮 真叫一个透心儿凉啊 不过凛冽的寒风也使雷雷的识识恢复了几分 见着周围没有路 连北北找不着 便跟随着二幺二吉普车留下的轮胎痕迹蹒跚而行 嗯 他连冻带饿 浑身无力 脚底下发飘 走得越来越慢 只好在一道沟边坐下来 在被风处躺下去 蜷缩起身子 凄厉的寒风从他头上嘶吼 卷起一层层黄土 而他背靠着沟坡 面朝着太阳 身上暖和了一些 他眯起肿成一条缝的眼睛 痴痴凝视着那一轮高高挂在天空上的白日 一阵抵挡不住的倦意袭来 脑子里没别的念头了 只想闭上眼睛睡觉 紧绷的神经一旦松弛下来 仿佛并非躺在土渠焊沟旁 而是睡在一张柔软舒适的席梦思大床上 阳光穿透了他紧闭的眼皮 呈现出温柔的粉红色 手雷肿胀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怪异而神秘 似乎梦中的一切都是那么完美 充满了温暖的色彩 他甚至梦到了前夜跟他绑在一起的女尸 连这个死人也是和善友好的 比起李斌等人 女尸更让手雷觉得可亲可近 但在转眼之间 女尸变了脸 又变成了狰狞恐怖的样子 一只眼珠子从眼眶中掉了下来 同时伸手抓住了他 手雷大叫一声 从梦中惊醒 睁开眼睛一看 发觉有两个人正在抓着他的衣领摇晃他 他恐惧的往后躲闪 一个跟头滚进了土沟 原来这二位是两个赶大车路过的 一个是车把式 另一个是跟车装卸的 拉了一车喂牲口的豆饼 二人坐在车源两边一路前行 装卸的偶然一撇 瞧见路边的土沟旁有一个人 急忙跟赶车的说 那边有个倒窝 车把是立即吁了一声 勒住大车举目观瞧 看不出来是死人还是活人呢 二人壮了撞胆儿 走上前去 伸手一试 发觉手雷还有呼吸 于是伸手拽晃他 没想到把手雷吓得够呛 一个跟头滚进了土沟 赶车的又将手雷拽上来 问他 你从哪儿来的 你躺这儿干嘛呀 手雷青肿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目光空洞无神 给对方来了个吃冰棍拉冰棍 没话 两个赶车的一合计 看这小子穿的破衣烂衫 身上还有伤 背不住 是从里边跑出来的 咱俩可得先稳住他 甭管什么来路 先弄到大队里去再说 二人打定了主意 蹲在手雷身前两米远 问道 你是哪个座上的 你是落难了还是怎么的 你倒是说句话呀 不说你从哪儿来的 我们怎么给你送回去啊 一听说要送他回家 手雷笑了 这个笑容却十分诡异 说不上是傻笑 疯笑还是坏笑 只能说是怪笑 赶大车的二位互相一看 决定先把这个装疯卖傻的人带去大队 连哄带骗让手雷上了大车 手雷瞧见车上有豆饼 疯了一样抢过来一个 用他那只没伤的手猛砸 那豆饼冻得邦硬啊 跟石头块一样 手雷拳头砸不动 又用胳膊肘 哪里砸得开来呀 只好抱住了啃 呲牙咧嘴的啃了半天 牙都崩出血了 也啃不下去一一星半点儿 两个赶大车的面面相觑 这个人饿疯了 居然连豆饼都吃 在过去来说 豆饼是喂大牲口的饲料 根本不是给人吃的东西 我们小时候经常可以看到公社大马车装了满满一车豆饼从市里经过 有那调皮捣蛋的孩子捡起砖头往大马车上砸 驶出百分之二百的力气 或许能砸下来一块豆饼 趁车把是没追过来 赶紧抱起豆饼跑回家 到家做一壶开水 把这一小块豆饼放在一个铝制饭盒里 用开水冲泡 盖好了焖一会儿 里边的豆饼就会变成了粥糊 再打开 一屋子豆香弥漫 有那家里条件好的呢 还可以往里边搁点红糖 白糖 古巴糖 那个年代孩子们都缺嘴儿 吃这个玩意儿也是觉得新鲜 可有一样 吃完之后放的屁特别臭 顶顶风都能凑出十万八千里去 赶车的车把是走南闯北见过世面 起初以为手雷是个疯子 此时一看 这是饿极了 这指不定几天没吃东西了这是还得说是乡下人 朴实善良 忙让那个卸车的从挎包里掏出干粮 两张发面饼 半个咸菜疙瘩头 手雷也没客气 接过来狼吞虎咽 噎得直翻白眼儿 车把是又递给他一个行军水壶 手雷连喝了几大口 这才把嘴里的干粮送下去 二人稳住手雷 互相使了个眼色 好歹把这小子弄回村里 如果说是逃犯 邀功请赏不在话下 如果是盲流 岂不又多了一个廉价劳动力 反正没什么亏吃 车把是松开车闸 挥动马鞭 把马赶向目的地 小东庄养殖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