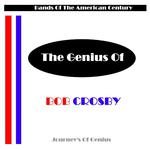本字幕由TME AI技术生成 第二百八十集 青色光线凝聚的白鹭昂首看了一样挂在墙上的标本 仿佛是在看一具玩具 睿智的双眼像看透了人生沧桑 举目间是道不尽的大道感悟 光禄试着抬了抬前蹄 循着记忆里的印记往前踏出一步 自嘲的说 哎 差点连路都往前走了 好歹要问是头鹿啊 沙发上的溪水睡得正酣 丝毫没有感知周遭这一变化 紧闭的额头不知道又想到什么棘手的难题 光禄打量着溪水 陆鼻喷出光砂般的鼻息 对着席水说道 听你爷爷话不好吗 听你的聪明才智 未来随便也是个名牌大学毕业的 先搞研究 顶尖高校里有你的独立实验室 想经商 四十岁不到就能身价千亿 想从政 核心圈子里也有你一个位置啊 为啥偏偏你就选了一条苦路呢 光影中的鹿叹了口气 艰难险阻犹如万仞的高山呐 你以为凭一本色字觉的册子就能普度众生了 哎呀 也罢 既然你我有缘 而我又欠你个淫情洁白的目录 接着说下去 我就带你去看一眼那个如同世外桃源般曾经的极乐净土吧 空气震颤起来 光影里的白鹭缓缓雾化 褪去成漫天的微光 像萤火虫一般漂浮在半空中 接着微光旋转起来 如同星云一般越转越快 快到看不清首尾 漏斗般涌向溪水的眉心 几个呼吸间 那构成白鹭的光芒通通消失在眉宇之间 没留下一丝光点 室内重回寂静昏暗 包括挂在墙上的鹿头 再没有什么光晕流转 仿佛之前那头乳白色的母鹿从未出现过一样 除了一个睡在沙发紧锁眉头而另一个撅着屁股像头熊 还把脑袋卡进了茶几角落的娃狗 睡梦里风带着呼啸 犹如刀片一般搁在脸上 烈烈作响的大风刮过头发 眼睛被泪水逼成一条缝隙 勉强看清周遭的景物 发现一团团黑影急速向后闪去 颠簸的路程在高低起伏间飞逝 像在狂风巨浪里的小舟 一下子被高高抛起 下一秒又重重落在背脊之上 震得五脏六腑像布口袋一样翻滚 好不容易看清一些周围的景象 那一团团转眼即逝的黑影原来是林间的树木 最细的都要两人合抱 参天的大树头盖下的树荫 像密不透风的黑色口袋笼盖在四周 天空是黑暗的 没有一丝光亮 溪水逐渐适应了颠簸 眼睛也勉强能睁开一丝 这让他一瞬间恍惚起来 明明不是已经天亮了吗 太阳已经升了起来 为何又变成了黑夜 这是在哪儿 感觉像是有一股稳稳犀利把自己牢牢的固定在马背上 问题是确定是马吗 身下的感知要比马背小上不少 几年前和老瞿头在游乐场里骑过马背要宽阔的多 不是马又是什么 溪水稍微抬起了头 迎着扑面而来的大风 看见眼前有几根树枝一样的东西 那是什么 是脚吗 马是不会长脚的 长脚的会是什么 仿佛是被背上的乘客估计捣乱 长脚的这个家伙常常打了个响鼻 放缓了些许速度 那高亢的幽冥仿佛在哪听到过 溪水紧紧闭紧双眼 又不管不顾的睁开 刮过来的风依然凌冽 带着一股好闻的填湿水气 这次终于看清了身旁的处境 在自己胯下的是一头通体雪白的白鹭 柔顺的皮毛在奔驰中犹如一朵绽开的雪花 雄健的躯体 裘捷的肌肉 昂扬的头颅 像坦克一样征服地势起伏的山路 却又灵巧无比在林木间穿梭 那犹如珊瑚般傲然挺立的鹿角足有半米之高 破开四周静谧的空气 黑色闪电般划开密不透风的阴影 溪水在短暂的错愕后 旋即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不是在现实中 而是在梦境里 身下这头犹如精灵一般的白鹭 正是之前挂在墙上和自己下棋的鹿手 他要带自己去什么地方 这里又是哪里 为什么要遁入梦中 他想告诉自己些什么 溪水苏醒后就牢牢攀住白鹭的脖子 缩在白鹭身后 但适应了四下里袭来的风后 更深刻认识到为什么说鹿才是森林里的主宰 两三米的林间洼地 只需要轻轻一跃就飞了过去 腾云驾雾一般 稍微低矮的树枝根本不值一审 鹿角挺立直接把枝压折断 再随意一甩就被抛到身后 经年累月累积厚厚的落叶 在如同残影般的鹿蹄四下翻飞 比马蹄更轻盈还更迅捷 哪怕前边并排一片密密的树干 也能迅速寻到其中的空隙一闪而过 溪水开始渐渐陶醉于这样的风驰电掣 这虽然不是做过最快的交通工具 但绝对是最赏心悦目的 那些近在咫尺的树影在眼前不断闪过 像被高级计算机精确计算过一样 毫厘不差的越过 风吹过发梢 带着空气里一丝微凉 季节也在变换 从深秋来到了初夏 天边露出鱼肚白 此时还漆黑的天空中万里无云 星星闪亮 一袭弯月掉在树梢 陆老头 溪水见白鹭渐渐放缓了速度 试着和他说话 想先搞清楚为什么把自己带进梦中 有什么用意 谁知道白鹭根本里都没有理洗水 放缓速度是因为前方地势没预兆的开始抖了起来 不适合再像林间那样的飞跃 周围的林木也稀疏起来 灌木开始越来越多 一窝窝的刺槐 胡丛肆意生长 翠绿的野草布满整面山坡 嫩绿的草叶上沾满尘埃的露水 白鹭往坡上攀爬 坡度陡峭起来 幸好土壤还算结实 吃得住一路一人的重量 白鹭继续向上 又半月半走了十来分钟 从这个高度往下看去 那片刚刚经过的密林已经缩小的犹如一块深绿色宝石一般 距离山顶越近 山上的植被越少 直到最后再也看不见一丁点绿色 空气也寒冷了不少 山上的风更刺骨 甚至一呼一吸间吐出白雾